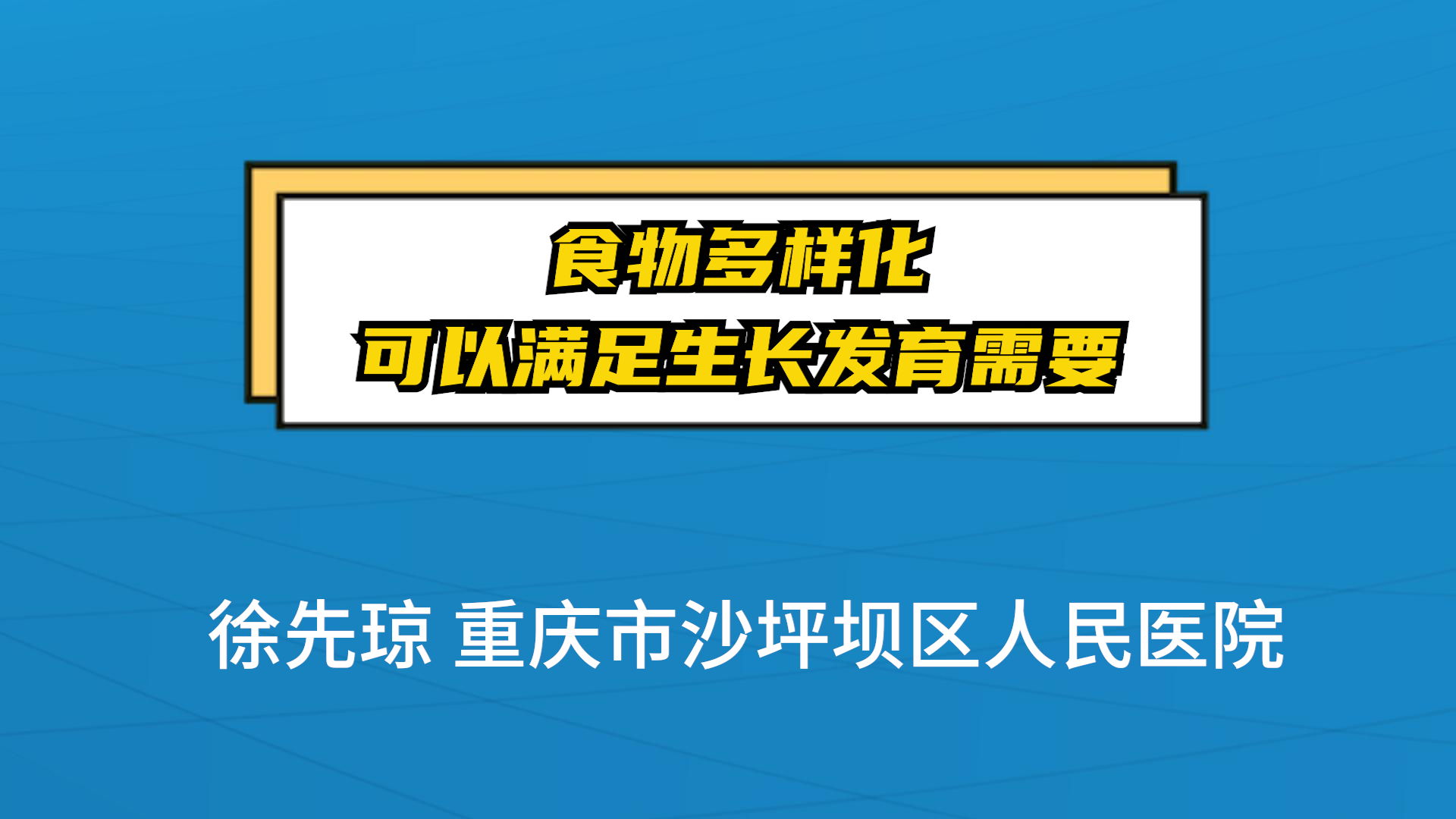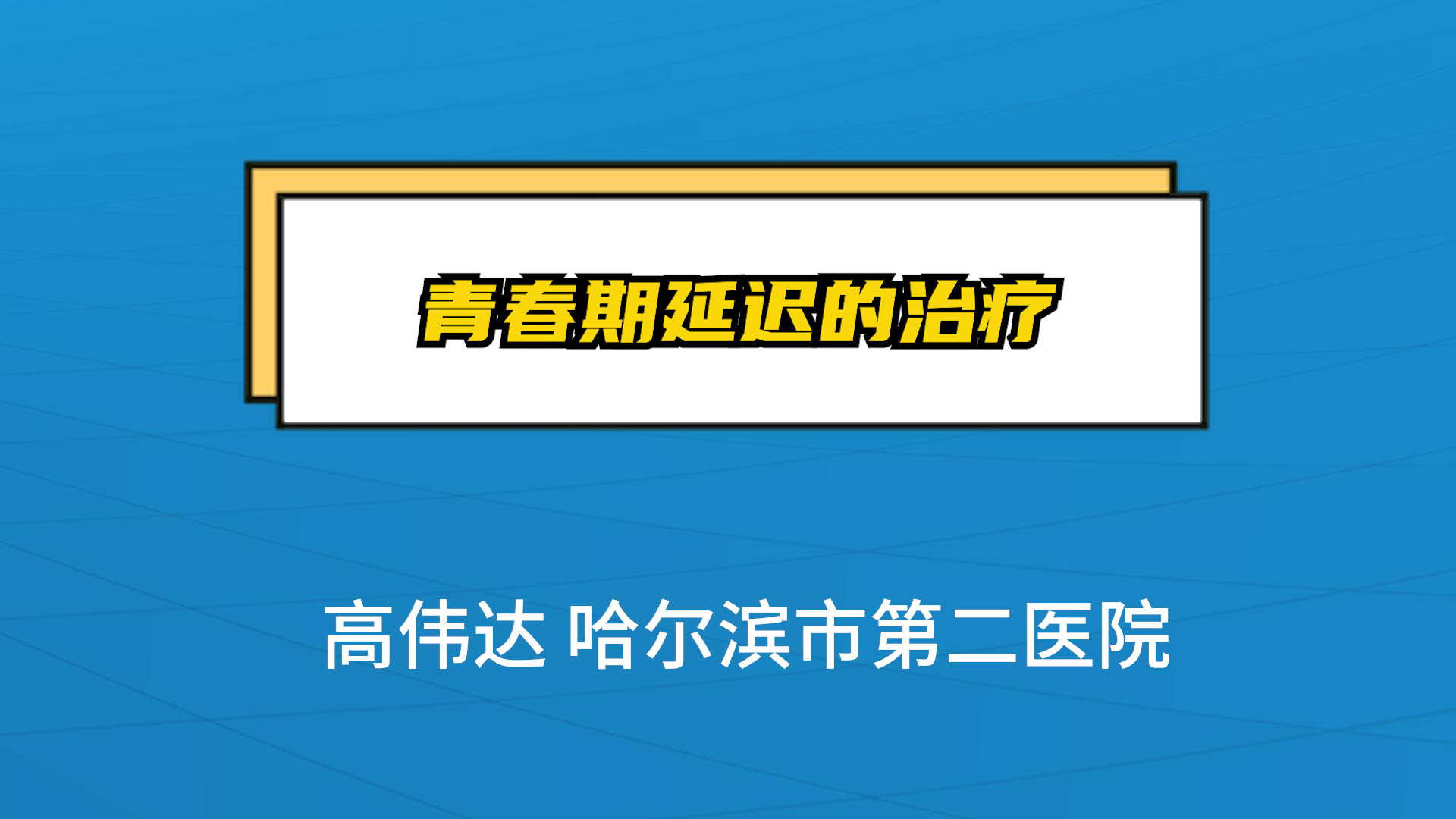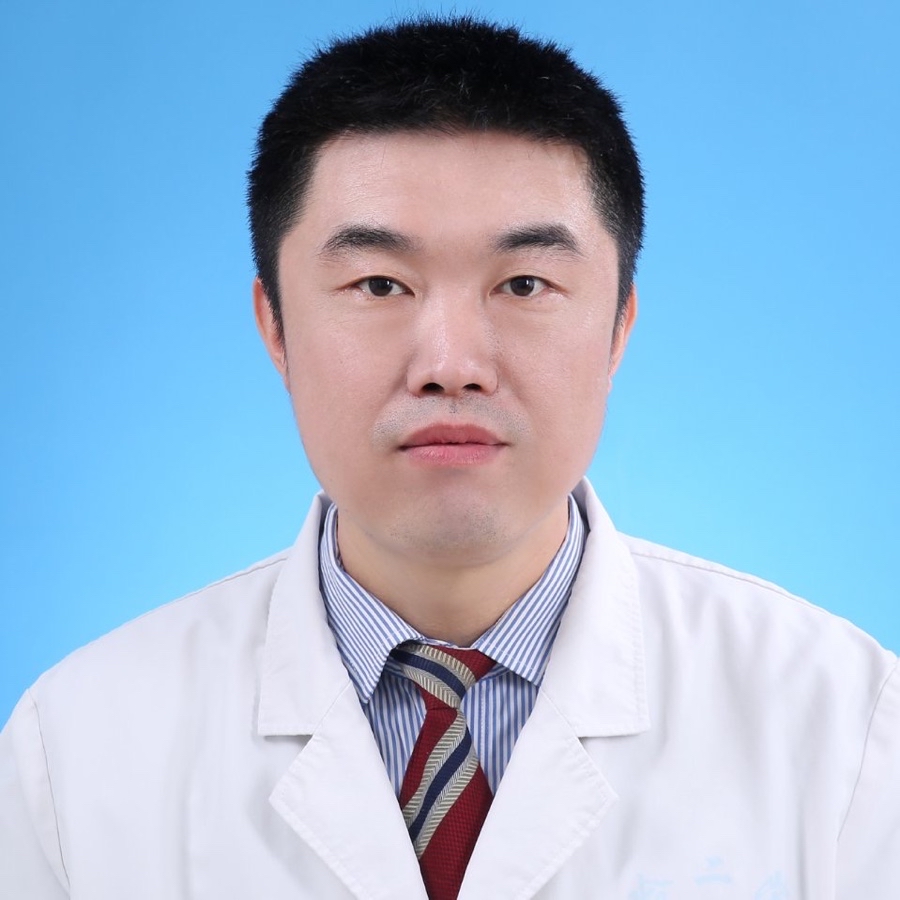试管婴儿多胎妊娠保胎药如何选择?
 健客医生官方号
健客医生官方号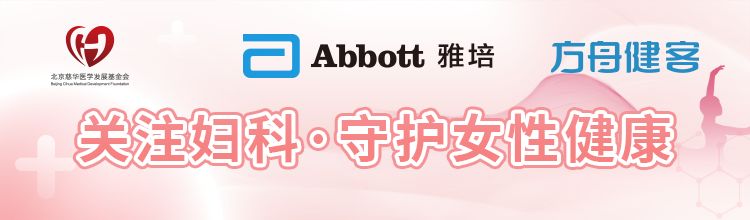
“试管婴儿”,双胎并不能带来双倍的喜悦。
在有些人的认知里,“试管婴儿”就意味着双胞胎,甚至是三胞胎!
一些不孕不育的夫妻,也把“试管婴儿”当成“一次性解决问题”的方法。不过在医学领域,双胎和多胎都属于高危妊娠,即使能成功怀孕,也会增加母婴的安全风险。
为什么医生不建议我选择双胞胎?
在二孩、三孩政策放开之前,许多不孕夫妻抱着“一次性解决问题”的想法,要求医生放置2个胚胎。在“试管婴儿”技术不太成熟时,也的确会通过放置2-3个胚胎来提高胚胎移植的成功率。
但是,多胎妊娠带来的风险也不可忽视:
l 对孕妈来说,双胎或三胎妊娠容易引起妊娠期高血压疾病、妊娠肝内胆汁淤积症、贫血、胎盘早剥、前置胎盘等问题,且发病早、程度重;
l 对胎儿来说,双胎或三胎致早产、难产、胎儿畸形风险也远远高于单胎。
因此,对于三胎或三胎以上妊娠者,必须进行减胎;而对于双胎妊娠者,若有基础疾病(妊娠期合并甲亢、家族血栓性疾病史、妊娠早期并发重度卵巢过度刺激)、疤痕子宫、有中期流产或引产史、子宫较小的情况,也建议患者减胎1。
多胎妊娠怎样安全减胎?
B超是目前早期诊断多胎妊娠主要的方法。
孕6周时可观察到多个独立的妊娠囊,其后约1~2周,妊娠囊中可以看到胎芽及搏动的胎心,孕11周时可显示胎头声像,多胎妊娠可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胎头。
当确定是多胎妊娠后,需要采用多胎妊娠减胎术,包括经阴道减胎术和经腹部减胎术。
减胎方法的选择主要依据减胎时的妊娠周数及绒毛膜性,比如孕早期时比较常选经阴道途径,孕中期则多用经腹壁途径1。
早期妊娠减胎术术后可使用孕激素进行保胎;若出现腹痛、阴道出血或异常分泌物、发热等症状,就要记得及时到医院问问医生哦!
不过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多胎妊娠。
现在,为降低多胎妊娠带来的母婴安全风险,改善妊娠结局,国家开始提倡单胚胎移植。根据相关指南规范,每周期移植胚胎总数不得超过3个,其中35岁以下妇女第一次助孕周期移植胚胎数不得超过2个2。
试管婴儿孕早期如何保胎?
上文所述,“试管婴儿”如果是多胎,可在孕6周左右能通过B超观察到多个孕囊,早期减胎术也一般于7-10周进行。1但在辅助生殖过程中,因为促排过程中使用激素诱发排卵、取卵时造成的刺激等原因,准妈妈黄体功能不全发生率高,导致正常妊娠难以维持,出现流产症状。
当出现先兆流产、复发性流产时,就不得不涉及黄体支持治疗。
黄体酮是目前临床用于黄体支持治疗的常见药物,常用给药途径包括肌内注射、经阴道及口服给药,但可能都会有一定不适。
比如肌内注射黄体酮需要每日肌肉注射,可能会导致注射部位疼痛和局部脓肿。3阴道给药则会导致会阴刺激、阴道分泌物增加、阴道流血、干扰性交等。4传统的口服黄体酮利用度低(<5%),且有嗜睡等明显副作用5,6。
这些传统方案的不便一定程度上“催生”口服地屈孕酮的诞生:口服地屈孕酮生物利用度更高7,8、日剂量更低9,可直接抑制子宫平滑肌收缩,起效更快10,患者依从性会更高。
高危妊娠患者如何进行口服地屈孕酮保胎?
除多胎妊娠外,复发性流产患者、有过早产史的患者等,都是高危妊娠患者。
在辅助生殖技术早期进行黄体支持可以改善妊娠结局,最新《孕激素维持妊娠与黄体支持临床实践指南》就建议口服地屈孕酮用于辅助生殖技术高危妊娠患者黄体支持10。
l 先兆流产患者和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患者
对于先兆流产患者和不明原因复发性流产患者,使用孕激素可以降低流产率,口服地屈孕酮可降低流产率及提高活产率,被优先建议。
患者服用口服地屈孕酮保胎时,需坚持服药至流产临床征兆消失、超声检查正常能停药,一般需服药至12周。
l 有早产史或者宫颈缩短的患者
而对于有早产史或者宫颈缩短的患者,无论单双胎均建议临床使用孕激素预防早产,从孕20周开始,直到孕35周停止用药,确保胎儿能在妈妈体内健康发育。
l 双胎、多胎妊娠患者
双胎、多胎妊娠伴前次自发性早产史的患者,也要根据临床实际情况选用孕激素治疗,以期降低早产率以及其他不良结局的发生率。
小结
“试管婴儿”助孕过程中,双胎和多胎妊娠带来的除了喜悦,也伴随着危险。在“试管婴儿”早期进行黄体支持可以改善妊娠结局,尤其对于多胎妊娠、先兆流产、复发性流产等高危妊娠患者来说,能够显著降低流产风险。
在黄体支持的各种药物中,口服地屈孕酮因为生物利用度更高、日剂量更低、起效更快、服用方便等优点,受到了患者和医生的一致建议。
此内容不可替代专业医疗建议、诊断或治疗。仅用于大众获取疾病和健康方面的知识科普,不能用于自我诊断病情,以上资料仅供参考,具体诊疗请到医院咨询专业医生。
参考文献:
[1]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.《专家共识:多胎妊娠减胎术操作规范》
[2]孙贻娟,黄国宁,孙海翔,等.关于胚胎移植数目的中国专家共识.生殖医学杂志.DOI:10.3969/j.issn.1004-3845.2018.10.003
[3] Janát-Amsbury MM, et al. Adv Drug Deliv Rev. 2009 Aug 10;61(10):871-82. [4] Tomic V, et al. Eur J Obstet Gynecol Reprod Biol. 2015 Mar;186:49-53.
[5] Stanczyk FZ, et al. Endocr Rev 2013;34(2):171–208.
[6] Shapiro D,et al. Reprod Biomed Online 2014;29:S1–14.
[7] Stanczyk FZ, et al. Endocr Rev 2013;34:171–208
[8] Paulson RJ, et al. J Clin Endocrinol Metab 2014;99:4241–9
[9] Tournaye H, et al. Hum Reprod 2017;32:1019–27
[10] 中国医师协会生殖医学专业委员会. 孕激素维持妊娠与黄体支持临床实践指南[J]. 中华生殖与避孕杂志, 2021, 41(2): 95-105.